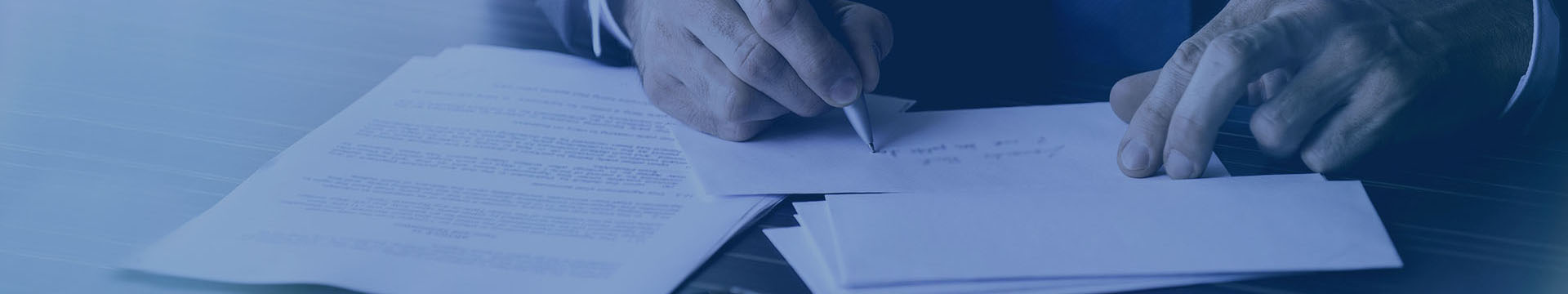
產業轉移是企業將產品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產地轉移到其他地區的一種現象。通常是發達國家或地區將處于成熟期、衰退期和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地區,一般體現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經濟發達區域向經濟落后區域轉移。
我國大體經歷了五次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一是建國后的產業資源集中調配和重點布局;二是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從國家安全出發的“三線建設”;三是改革開放后由內地向沿海地區的轉移;四是21世紀后,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從頂層設計層面引導產業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五是近年來在大國博弈和全球產業從中國內地向國外轉移的背景下,國家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出發,進行深入布局調整的新一輪產業轉移。每個階段的產業轉移都具有與時代緊密結合的經濟特征。當前,新一輪產業轉移也呈現出新時期的時代特征。
2024年9月25日,國家層面印發《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這意味著,我國中西部地區迎來了新一輪承接產業轉移的歷史性發展機遇期。當前,我國東西部產業轉移的要素優勢減弱、梯度動力降低、協同意愿增強、立體化轉移和產業水平分工趨勢明顯。如何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地把握當前機遇成為中西部地區“十五五”時期的重要課題。
一、重視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新特征
當前全球已進入第五次國際產業轉移,產業轉移的動因、流向、特征、形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受大國博弈疊加疫情及俄烏沖突影響,部分地緣政治風險已經轉化為直接成本,對原有產業布局形成極大破壞。全球產業體系加速分化重組,發達經濟體關鍵領域“重點回流”,政治、安全等非市場因素成為影響產業轉移的新的決定性力量。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我國部分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現象增多,我國產業體系完整性和產業鏈安全穩定面臨新的挑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的協作機制,推動轉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由此可見,我國新一輪產業大轉移與以往的最大不同在于國家“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的戰略需求,代表著國家高層更深層次的戰略考量。
在政策和市場雙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國新一輪產業轉移呈現雙向化、立體化、新質化等新特征。首先,新一輪產業轉移是轉出地與承接地的要素雙向流動、產業雙向協同發展,產業轉出地和承接地之間的聯系比以往更加緊密,相互之間的依賴性也明顯提高;其次,新一輪產業轉移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產業鏈低端環節的轉出,而是細分產業鏈的立體性轉移,是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并存的產業轉移,在轉移過程中伴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迭代。產業承接地從“被動承接”到“主動升級”,突破垂直分工的產業轉移的意圖更加強烈;最后,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綠色化發展等新質化特征明顯。在我國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策環境下,產業轉移過程中普遍引入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制造”向“智造”轉型;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主動與“雙碳”目標結合,高載能產業進一步向清潔能源富集地區轉移。
二、樹立高質量承接產業轉移的新觀念
產業轉移決不是往“低處”搬家,而是向“高處”發展。產業轉移常常讓人錯誤地認為是企業從發達地區往欠發達地區搬家。事實上,產業轉移的核心動因從來都是企業在解決向“高”處發展的問題。要么是看重欠發達地區較低的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要么是到更靠近原料資源及供應鏈重組地區降低采購及物流成本,要么是高載能產業更靠近綠電和新能源富余地區獲得較低的電價和更寬松的政策空間,這種產業轉移的本質是企業追求更高的生產利潤、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好的發展前景,代表著資金、技術、勞動力的重新分配,是生產力布局的空間優化。如果一個相對落后地區無法為企業的發展帶來益處,不可能對轉移產業形成吸引力。
產業轉移的承接不僅是單項要素優勢和靜態資源優勢的比拼,更是自身系統優勢和動態新優勢的塑造。在新一輪產業轉移中,僅依托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優勢形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梯度轉移,越來越無法跟上時代發展的進程。承接地區單一要素的成本優勢常常被系統性劣勢所抵消。政策、安全等非市場因素,以及產業發展系統性成本、技術創新和服務體系成為新時期影響產業轉移的重要力量。特別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承載條件有限,普遍存在園區建設水平不高、營商環境友好性不足、產業生態及鏈條配套不健全、公共服務及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人才科技等創新要素短板明顯、運營模式和招商理念滯后等現實問題,導致無法為轉移企業創造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更好的發展空間,嚴重降低了產業轉移的意愿。
三、善用高質量承接產業轉移的新策略
高質量承接產業轉移要體現產業承接的適宜性、高效性、成長性、體系性、戰略性特征,必須強調“占位要高;眼界要寬;動力要變;機制要活;特色要足;結合要緊”,使轉移產業“接得穩、留得住、長得好”。
01- 突出獨特性高點占位
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動因不僅要靠市場驅動,更要靠政策驅動、靠中央支持。承接產業轉移要著眼于“兩個大局”,彰顯自身“在我國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平,加快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搶抓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和關鍵產業備份等戰略機遇,找準自身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價值定位,爭取國家級產業轉移示范區等相關政策與資金支持。
02- 強調系統性承接謀劃
通過高點占位找到政策支點后,要擺脫簡單化、粗放式的招商模式,精準策劃重點產業及產業鏈承接方向,統籌布局重點承接園區及功能平臺,系統設計重點產業鏈條、轉移對象、招商模式、合作機制、產業配套與城市服務等。強調以政府引領、市場化運營,引導、設計產業(鏈、群)發展邏輯,重塑產業生態及創新發展“空間”。
03- 打造典范性承接模式
探索與東部地區建立產業協作、開放協同和利益共享機制,形成產業合作、園區共建長效機制。努力構建利益共享的跨區域協作機制,打造“事業共同體”,變“對口幫扶”為合作共贏。聚焦代表性領域,集中資源,打造典型模式和標桿園區。例如,云南省自貿試驗區昆明片區與上海臨港集團共建滬滇臨港昆明科技城,在昆明集合上海臨港的招商、研發、市場優勢,疊加自貿試驗區政策、產業、場景優勢,通過“上海企業+云南資源”“上海研發+云南制造”“上海市場+云南產品”“上海總部+云南基地”的合作模式,打造“東西協作、產業協同”標桿園區;再如,云南紅河州以綠色紡織發展為核心,以“東部技術+紅河制造+越南組裝+世界市場”為發展方向,探索“一企兩國三廠”跨境產能合作模式。其龍頭企業新東旭分別在開遠、河口及越南福壽省投資建設三個廠,依托開遠能源優勢進行面料生產,依托河口的跨境人力資源優勢降低縫制工廠勞動力成本,河口生產的產品到越南進一步加工后再出口,規避了歐美國家的高額關稅,通過“三廠”緊密協作、聯動發展,實現“東部技術、紅河面料、越南服裝”的產業鏈重新構建,形成了面向東南亞、歐美國家紡織服裝生產出口的完整產業鏈。
04- 嘗試經營策略創新
隨著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代表著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邏輯、新范式不斷涌現,為承接地區創新發展路徑提供了機遇。例如,云南可以憑借自身豐富的物種資源直接接軌國家級生物技術研究和布局;基于獨特的自然條件、物流需求和已有通用機場資源,爭取國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試點,鏈接、支撐、服務和融入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創新工程及戰略布局;以應用場景創新和大規模示范應用為牽引,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中,與發達地區實現并跑、跟跑。通過設立產業基金等方式增加招商引力,強化柔性引才能力,破解自身投資與人才短板。營造“全程陪跑”型承接環境,讓一流環境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最好名片。
丁 偉

高級咨詢師
圖片
長期專注于區域發展戰略、產業研究與規劃,城市更新與園區項目咨詢。近年來作為主要負責人完成云南省"十五五”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思路研究、昆明市現代流通戰略支點城市建設方案、江川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等項目。
編輯:張 華
審核:劉 燦

